绞刑架下的报告(绞刑架下的报告课文)
绞刑架报告(绞刑架报告文本)
▲2019年9月10日,在捷克富奇克协会参加《报告》展览。左一为作者,左三为捷克富奇克协会主席杰尼内克。
2019年9月8日,捷克布拉格,我们一行人开始了《绞刑架下的报告》的重读之旅。这一天是捷克反法西斯战士、作家和记者尤利乌斯·伏契克的牺牲纪念日。1943年9月8日上午,他在德国柏林布洛琴斯监狱被纳粹杀害。他只有40岁。傅奇克于1942年4月24日夜被捕,并被立即带往佩克塞宫,那里是布拉格盖世太保的总部所在地。当时的傅其科留着胡子,在刑讯逼供的审讯过程中,他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直到被汉奸指认。之后被关押在布拉格郊区的Punkratz监狱,在那里用铅笔在纸片上写下了举世闻名的不朽著作《绞刑架下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2019年9月11日,捷克民族博物馆档案馆展示报告手稿。
丢失的一页手稿
秋天的布拉格,在傅琦克的笔下是金色的。9月10日,我们在捷克傅奇克协会详细了解了傅奇克报告75年来的出版历史。
这份报告的发现是偶然的。
1945年5月,希特勒的德国宣布战败,战争结束。被纳粹囚禁在柏林以北80公里的拉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的古斯塔夫·傅奇克重获自由,回到布拉格。当时她无法接受丈夫傅其科已经遇害的事实,四处打听他的消息。6月9日,傅其科的姐姐利勃海尔在《红色力量》上发表了一篇《寻找你》。那些想知道有关傅奇克被捕的任何细节的人写信通知她和傅奇克娃。几天后,有人回信,附了一份关于傅其科的“旁证和介绍”。写信人说,这份材料是一位中学校长约瑟夫·佩斯凯(Joseph Pescheck)转发给她的,佩斯凯曾经和傅奇克关在同一间牢房。不幸的是,他还没出狱就在狱中受尽折磨,回到祖国就去世了。在这份文件中,Pescheck说他和傅奇克一起被关在Punkratz监狱的267号牢房,他们建立了父子关系。傅奇克称他为“爸爸”,并告诉他,他的监狱笔记和案件材料都交给了一名捷克看守科林斯基,由他代为保管。
富奇克娃立即开始寻找科林斯基。在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最终找到了住在布拉格60公里外的科林斯基。他给了傅其科娃几张长长的、泛黄的纸,上面是傅其科的笔迹。这些纸片的每一页都标有号码:左上角是136-141,右上角是一个“R”字母。傅琦可问,还有其他小纸片吗?科林斯基说他要把它们找回来,因为他藏在不同的地方,其中一个在洪波利兹。
与此同时,根据他人提供的线索,富其克娃于7月初前往布热诺夫,找到了一个名叫斯科雷波娃的女子。她从藏在地窖土豆堆里的长方形铁盒里抽出一叠小纸片,上面有傅其科的笔迹。斯科雷波娃女士告诉付启科,这些小纸片是她丈夫寄给她的。当时,她的丈夫在Punkratz监狱做杂工。一个名叫雅罗斯拉夫·霍拉的捷克看守经常给他带来一些囚犯写的信,让他设法把这些信寄回家藏起来,其中有7页傅奇克的手稿。斯科雷波娃的丈夫在1944年被枪杀。
付启科拿到的这些小纸片,左上角标有页码78-84,右上角标有字母“R”。几天后,傅奇克娃拿到了150多份傅奇克手稿,上面有科林斯基找到的页码。在第一页上,傅企克写道,“绞刑架下的报告——JEF——写于1943年春天,地点在彭克拉茨的盖世太保监狱。”然而,富奇克娃发现,科林斯基和斯科雷波娃女士一起保存的手稿还少了一页,也就是第九十一页。

即便如此,1945年10月,这份封面设计简洁震撼的报告正式出版,立即吸引了捷克乃至全世界读者的目光。仅仅几个月,第二版就发行了,虽然还是缺了一页。
1946年春,傅其克正在布拉格参加一个青年集会,一个15岁的女孩找到她,告诉她自己是洪博莱茨人。1945年春,她拜访了扎·沃卡夫妇在洪·博勒茨的家。当她听说庞兹拉克的一个狱警委托他们家保管傅其克的一些手稿时,她要求看一看,于是主人把它们从密室里拿了出来。后来,女孩拿走了一本书里她没有看完的最后一页,然后她把书借给了别人。直到最近,那本带着那张小纸片的书还了回来。那张小纸片是手稿的第九十一页。之后第十版终于补齐了缺页。
后来傅其科娃还发现了另外8页傅其科的手稿,每页右上角都有一个“L”字母,都是和文学有关的。现在可以确定的是,“L”是“文学”一词开头的第一个字母,而标有字母“R”的167页是“报告”一词开头的第一个字母,即“绞刑架下的报告”。
自1945年首次出版以来,该报告已在捷克共和国出版了36版。随着岁月的变迁,报告的发布与时俱进,越来越完善。
▲1945年报告第一版
异常困难的写作过程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捷克国内就出现了否定傅奇克的趋势。9月13日,我们在拜访《为喜而生》第一本傅琦克传记的作者、作家、文学史家、艺术评论家格里加尔时,他向我们介绍了这一潮流的来龙去脉。他深有感触地说,“对傅琦可的尊敬,已经被一阵诽谤和最卑鄙的谎言所取代——傅琦可不再是英雄,而是叛徒;不再是无畏的抵抗战士,而是懦夫;绞刑架下的报告不是他的作品,是别人伪造的赝品。在我看来,这是对傅其科的第二次处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群捍卫傅企克荣誉和精神的人聚集在一起,对报告进行了专业而深入的研究。
1991年,捷克富奇克协会成立。协会成立之初,以抢救的方式采访了目击傅其科写报告的相关人士。
由于科林斯基已经去世,他们在战后阅读了他写的一系列感言。在科林斯基的材料中,傅其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信任他,把带给他的铅笔和纸藏在他牢房的草地里,但从来没有用过。直到一个多月后,1942年6月初,傅其克从佩采克宫回到彭克拉茨监狱,遍体鳞伤时,科林斯基才建议他再写点什么。他告诉付启科,不是为了现在,而是为了未来,让你所知道的一切不会随你而消失。这一次,他的话打动了傅其科,让他相信科林斯基是“我们的人”。傅企克最早写的是标有“L”的文学批评部分,直到1943年3月底4月初才开始写标有“R”的报告。写作很难,只有在科林斯基值班而且是白班的时候才能完成。他会轻轻敲敲关押傅其科的二楼267号牢房的大门,示意傅其科可以开始写作了。付启科写作时,在牢房周围巡视。一旦有事,他马上敲两下,告诉傅其科停止写作,把稿子藏起来。写完后,傅其科会去叩叩,把小纸片交给科林斯基,铅笔总会一起还回来。科林斯基立即将这些手稿藏在监狱厕所连接水箱的水管后面,然后在晚上下班时藏在皮包盖的亚麻内衬里,以防狱警检查他的皮包。他帮助柯林斯基·傅其克写作,并将手稿送出监狱,直到1943年4月,因盖世太保典狱长索帕的怀疑,被转移到三楼监狱。
捷克看守雅罗斯拉夫·霍拉(yaroslav Hora)从1943年2月到同年12月,在庞克拉茨监狱服刑十个月。他因协助囚犯被捕,先后被送往毛特豪森集中营和古森集中营。他在接受富奇克协会采访时说,他和科林斯基在二楼监狱值班,他们经常互相帮助,一起工作。柯林斯离开时告诉他,傅其科正在写作,让他把铅笔和纸送到他的牢房里,并替他守着,以免被发现。即便如此,这也常常是危险的。有一次,盖世太保突然从一楼跑上来,直奔二楼傅其科的牢房。霍拉报警给付启科已经来不及了。正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傅企克冒着极大的风险进行写作。每次写完,他就把手稿连同铅笔一起交给霍拉,霍拉马上把它藏在厕所里,下班后从监狱里拿出来,然后在街上或电车里交给科林斯基。1943年5月,傅其克再次被带到佩采克宫受审,盖世太保告诉他,他的案子已经移送法院审理。这种情况表明,他将很快离开Punkratz监狱,被带到德国的纳粹法庭。有鉴于此,傅企克决定将自己的监狱作品大幅缩短,尽快完成,以免成为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因此,他加快了写作进度。6月9日,得知第二天就要被派往德国后,他全力以赴,一口气写完了最后一章和全部作品。6月10日,傅其科被转移到德国。他被关押在Bautzen监狱、柏林刑事法院监狱和Blochens监狱,不久后被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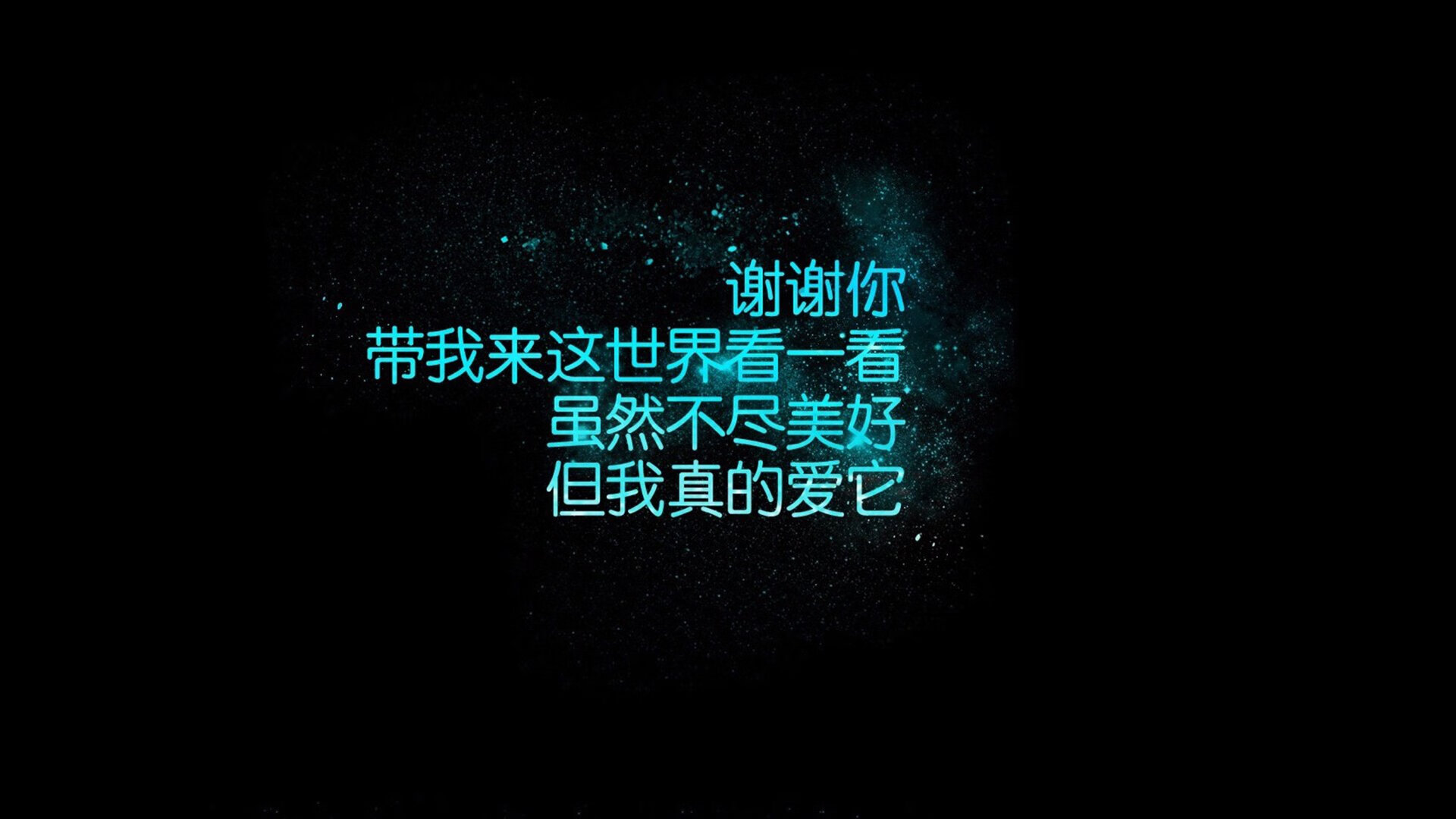
▲1994年的报告全文
富奇克一个无辜的富奇克协会也通过对霍拉等当事人的采访,证明了报告的撰写是毋庸置疑的。
此时,捷克公安部对傅其科的举报笔迹进行了鉴定,最终确认了其真实性。如今,傅奇克的手稿保存在捷克国家博物馆的档案馆里。9月11日,在档案室,傅其科的女馆长和两位档案员、研究员给我们展示了夹在玻璃板里的报告手稿,并向我们介绍了笔迹鉴定的过程。在监狱里看到傅其科写的稿子,我们非常震惊,深受感动。
公安部笔迹鉴定结果出来后,傅企克协会就傅企克的报告召开了国际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公布了该报告的所有手稿,包括该报告以前所有版本中删除的一些文字和段落。这些被删除的文字和段落,只是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作为否定傅其科的借口。
专家学者认为,1945年付其克的报告发表时,删除这些文字和段落是可以理解的。第一,战争刚刚结束,报道中写的一些人还在筛选中,不适合发表。第二,人们沉浸在庆祝纳粹德国覆灭的喜悦中。傅其科在报道中对德国人民的高瞻远瞩的宽容和善意,至今仍不合时宜。第三,接受德国看守的半支烟等细节可能不符合英雄人物的塑造。第四,由于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写作,面对生命最后日子的临近,傅其科为了赶稿,不得不用简洁隐忍的笔触,尤其是作为一个紧急章节的最后一章,所以未能作出具体的描述,清晰细腻地描述他如何通过“做一些与以往不同的事情”和“演一出精彩的戏”来对抗盖世太保;如何巧妙应对盖世太保,想尽办法误导他们“忙着抓幻影”。这些没有叙述的文字,如果不放在当时的语境中,很容易产生误读,有可能损害傅琦可的形象。其实我们认为,今天读起来,这些文字更能凸显傅奇克写作的苦恼与艰辛,更能凸显傅奇克勇敢、忠诚、乐观、冷静、机智、诙谐的人格魅力,丝毫不影响他作为反法西斯英雄的伟大与荣耀。事实上,留存于世的秘密战时著述,在出版时总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和Het Achterhuis一样,它的出版也经历了从删节到完整版的漫长过程。
傅企克协会通过查阅历史档案,采访多方,证明傅企克不仅没有背叛任何同志,还保护了一批有志之士免受盖世太保的追杀。与此同时,他在狱中坚持对敌斗争,团结号召狱友坚定信念,乐观向上,以坚忍不拔的精神迎接胜利。1993年,傅企克协会将采访视频制作成纪录片《证词》,公开发行。
1994年,傅企克协会认为发表全文报告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各种理由都不存在了。因此,向读者呈现一份完整的、具有原创性的报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及时的、必要的,尤其是当那些不实之词能够迷惑年轻一代的时候,因为他们亲自了解这位具有世界声誉的同胞的真相的可能性非常小。”这是Oleko出版社全文发布该报告的真实背景。全文共七部分,最后一部分是捷克公安部对傅其科笔迹的专家鉴定复印件。
▲2008年报告手稿版
研究结果发人深省。
在捷克,有两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很早就开始了对傅奇克报告的严谨细致的研究,并写出了极其详尽的评论。1930年出生的亚纳切克和1924年出生的哈伊科娃,以包括历史学家、文学史家、语言学家、校对员在内的知识渊博的专业人士团队,从纳粹占领时期的捷克抵抗运动史入手,严格遵循科学的史学方法,挖掘和整理了许多细节,有了许多新的发现。他们还创造性地讨论了纳粹占领时期抵抗运动迄今为止很少探讨的复杂方面,促进了报告的研究。两位历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者应该感受人们在极端情况下的思想和行为,重构以前发生过的重要事件和历史过程,认识事物的意义,勾勒出历史过程中隐藏的趋势。1995年夏天,他们发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即该报告的第一个全文评论版。他们计划在未来继续推动他们的研究工作,并不断推出更新版本。为这本书写结语时,亚纳切克觉得他正在完成自己的终身使命。的确,这本书刚出版,他就全力促成了他在当年12月突发心脏病猝死。哈伊科娃继续他的研究,直到2012年8月去世。2016年,课题组推出了该报告的第二版全文评论,增加了最新的发现,为加深人们对傅奇克和整个捷克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了解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他为第一份报告的全文评论版所写的后记《怀疑与证实》中,亚契克郑重地写道:“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所看到的关于《绞刑架下的报告》(也是关于占领国的地下斗争和整个制度)的最重要的信息可以清楚地概括为一句话:许多事情有其他的真相,但绝不是完全相反的。”这为付启科实现了公正、公平、正义。
傅企克报告的研究结果发人深省:虽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傅企克当年的神话宣传应该被重新审视,但让一个英勇牺牲的反法西斯英雄来承担被后世神话质疑甚至否定的结果,是不客观不公平的,现代社会制造种种神话也是不可接受的。历史记忆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湮灭,也不会被随意篡改。正如著名出版人、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委会原副主任叶至善所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人们心中抹去一个像傅企克这样的反法西斯战士。”
▲2016评论版报告
相关链接
《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一些中文翻译
傅其科的报告充满了英雄主义和人性,感动和鼓舞了全世界数百万追求真理、自由和正义的读者。现在,这部杰作已经被翻译成9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版。在傅企克协会,我们介绍并展示了该报告中译本的出版。
1947年,《大连真理报》社长谢德明邀请翻译家刘辽义翻译这本书。刘辽义根据莫斯科《真理报》出版局1947年出版的俄文版翻译为《火星系列》,以《死囚日记》为题在《真理报》连载。1948年2月,光华书店(后为三联书店)在大连出版单行本。书名改为《绞索勒住脖子时的报告》,初版3000册。这是该报告首次以中文成书在中国出版。在这本粗制滥造的《战争中诞生》中文版的封底上,有傅其科写的一句话:“与其使我的报道成为时代的证据,不如使它成为人的证据。我认为这很重要。”
▲1948年2月光华书店刘辽义译。
1951年2月,三联书店在北京重新整理出版了刘辽义译本。这一次,题目是“当绞索套在脖子上时报告”。
▲刘辽义译三联书店1951年2月
195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上海出版了由陈翻译、冯至校订的《绞刑架下的报告》。这个版本是根据1947年出版的法文版,参考1951年柏林出版的德文版和1952年莫斯科出版的俄文版翻译的。这是中文版第一次使用“绞刑架下的报告”这个标题。
▲195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陈译。
197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蒋翻译的《绞刑架下的报告》,这是该报告第一次直接从捷克语译成中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蒋译1979年9月。
1995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捷克奥列科出版社出版的报道全文。中国青年出版社是国内第一家与捷克驻华使馆取得联系的出版社,邀请了许耀宗、白梨树翻译,以保证在9月8日傅其克壮烈牺牲纪念日之前出版。1995年8月,中国青年学会出版的全译本在中国与读者见面。








